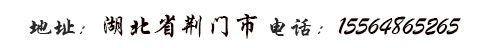封磊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
|
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基于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与方志的互证性研究 封磊 基本信息 提要:清代内阁刑科题本对底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丰富的记载,是难得的社会史、生活史资料。通过对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中陕西籍命案当事人交代的家庭人口、年龄、子女、婚育等描述性资料做统计性分析,揭示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家庭规模、婚育状况、生命周期等基本样态;结合对刑科题本中案发人的生计的考察,与方志进行互证性比对研究,揭示清中叶陕西不同区域底层民众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日用等的生存面相,并思考地域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趋向。 作者简介:封磊,年生,咸阳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文章原刊:《中国地方志》年第5期。 21世纪以来,伴随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尤其是以微观视角考察个人的日常生活,以此窥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文化意义,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已取得可观成果。就群体而言,多集中于官吏、士绅、塾师、文人等有识阶层;就地域空间来说,多集中在东部城市,而对中西部地区及民族地区关照不足。一来因有识群体留存资料较多;二来因其社会作用较为显著,对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感知敏锐,往往成为研究者重视的群体。但同时也说明一个明显的缺憾,即在理念和方法上对占社会群体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忽视。当然,这也有其内在原因,底层普通大众因其受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对习焉不察的“日常”注意不够,文字留存较少。这对以文本为主要载体的史学研究来说,史料上的“无征不立”仍然是瓶颈所在。年出版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全三册,以下简称《辑刊》),因是官方记载命案的司法文本,详实地记载了区域社会中大量底层民众的身份、年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社会关系与案件情节有关的生活内容,颇具日常生活特色。已有学者就此展开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这些真实的命案题本,不仅可以探知个体的生活史与生命史,为研究特定区域普通民众的生活史提供了直接史料,还可借鉴社会学的随机抽样法,将描述性的资料做统计性分析,以深入认知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集体群像与生活样态。本文即以《辑刊》为中心,并比对地方志进行互证性研究,探讨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在生命周期、生计格局与生活样态,以就教方家指正。 一、资料来源与分析:案件分布、婚姻家庭与生命周期表1《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陕西籍资料表 序号 年/月 府州县 标题 页码 1 2/8 汉中府南郑县 民李澍修因借钱纠纷伤缌麻服兄李瑞征身死案 4 2 5/4 兴安府安康县 民王学武等因争种地亩殴伤缌麻服叔王淮身死案 12 3 8/8 凤翔府宝鸡县 民毛建业因拆公共房屋扎死大功堂兄案 49 4 8/10 同州府蒲城县 民刘元林因索欠打死刘元恺案 53 5 8/11 西安府富平县 民窦景顺因口角打死无服族弟案 56 6 10/2 兴安府安康县 民杨世友因分账不清打死胞兄案 86 7 10/4 汉中府南郑县 僧人杨元喜因口角致兄长自跌身死案 94 8 11/5 西安府咸阳县 民杨景文因被说破偷麦事谋杀胞兄身死案 9 14/11 同州府郃阳县 民柳学义勒死妻子李氏移尸图赖王孟科案 10 16/1 同州府韩城县 民卫创升等共殴无服族侄卫连城身死案 11 16/3 同州府朝邑县 民侣泳强因找价纠纷殴伤吕永幅身死案 12 16/5 延安府肤施县 民杨助清为索分钱财扎伤无服族兄杨锐身死案 13 16/9 凤翔府凤翔县 民张世魁因盖草棚事致伤堂侄身死案 14 19/3 邠州直隶州三水县 民傅智丰抓伤无服族兄傅作栗致死案 15 21/2 邠州直隶州三水县 民郭更有儿因其母被强嫁伤小功服叔郭文智身死案 16 21/3 兴安府安康县 民赵文科因占种纠纷误伤其妻刘氏身死案 17 22/10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李学因争分族内绝产殴伤小功服兄李荣身死案 18 23/3 延安府绥德县 民贺惠因索讨欠钱殴毙缌麻服弟贺盛案 19 23/10 西安府孝义厅 民杨范书勒死妻子吕氏移尸图赖案 20 24/7 同州府韩城县 民陈九恩因不肯归还田地被胞弟陈九伧殴毙案 21 9/12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秦邦贵因其妹被打致死妹夫之弟案 22 10/8 汉中府西乡县 民刘光彦因索欠事将儿女亲家王启太致死案 23 19/2 西安府富平县 民韩登顺等因分家将韩有顺砍伤身死案 24 24/1 兴安府安康县 民赵金索欠殴伤妹夫张纲身死案 25 6/12 同州府华县 民陈来珠儿等共殴仲名身死案 26 7/2 西安府周至县 民辛其正因索要地价被邻村人安三友打死案 27 8/1 榆林府怀远县 民胡交年子因口角打死宋起德案 28 8/7 同州府蒲城县 张庭英因索欠打死同街人靳学案 29 10/8 西安府长安县 民高仁吉因调节他人事将乡邻张江致死案 30 11/12 西安府周至县 民高改生因索欠并被辱伊妻致死邻村段六案 31 15/4 西安府富平县 民赵德元为索欠银殴伤惠有顺身死案 32 15/7 同州府大荔县 民潘贵玉等为索谢银共欧同村人吴成都身死案 33 15/12 西安府泾阳县 民王居礼因债务纠纷殴伤同村人刘维宁身死案 34 17/10 西安府咸宁县 民周元才等因口角共欧邻人致死案 35 21/6 汉中府略阳县 民张均因利息数额之争将梁自正扎伤身死案 36 22/3 西安府咸宁县 民孙世奇因欠地价未还被同村人孙成刚殴毙案 37 22/5 西安府咸宁县 民屈周因清理地价钱文被崔世元殴毙案 38 24/2 凤翔府凤翔县 民苏文炳因索讨当地契约殴伤同村人王贵身死案 39 4/10 商州直隶州 民吴金玉因索欠打死湖北孝感县民杨添禄案 40 5/4 汉中府留坝厅 民郭凤因索欠被四川万县民秦得荣打死案 41 7/1 兴安府旬阳县 民李有因买木材打死吴九案 42 8/1 汉中府宁羌州 民张银因工钱打死四川中江人锡继春案 43 9/2 榆林府怀远县 民刘文裕因索讨钱文事被米脂县民折金竺殴伤致死案 44 9/5 鄜州直隶州宜君县 民蒙茂泰因索欠钱文被客民霍俊礼扎死案 45 9/6 汉中府宁羌州 民傅洪太因分争卖猪钱打死杨登贵案 46 13/4 商州直隶州雒南县 民茹添得因稞种地亩纠纷砍死山西虞乡县邢养得案 47 13/9 汉中府洋县 民樊正海谋害张珑案 48 14/10 兴安府石泉县 客民徐尔华拖欠工钱被客民廖正坤等共殴身死案 49 14/11 兴安府安康县 客民谈开礼殴伤舒庭幅身死案 50 15/3 鄜州直隶州宜君县 薛成因田地纠纷被寓民郭英踢伤身死案 51 15/7 汉中府定远厅 蒋开运因劝架被湖南衡阳县范占鳌扎伤身死案 52 15/12 汉中府定远厅 民张兴才殴死佣工张泳成并杀人灭口案 53 15/12 鄜州直隶州宜君县 赵举因债务纠纷被客民郭成积戳伤身死案 54 15/12 商州直隶州 民余道和因租佃事致伤刘添才身死案 55 16/3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邢立成因财务纠纷被客民李贵砍伤身死案 56 16/3 兴安府旬阳县 民宁郭宾被宁士成殴伤身死案 57 16/3 汉中府南郑县 民杨魁选为索讨工钱砍死客民柳泰案 58 16/3 同州府华州 蔺兴才因种地纠纷被客民董景端等共殴身死案 59 16/4 兴安府安康县 民王兴顺因索欠启衅谋杀任世兴身死案 60 16/6 兴安府安康县 民刘茂魁伤詹开贵身死案 61 16/12 商州直隶州 民朱三娃子因索要工钱事踢伤雇主田兴潮身死案 62 17/2 汉中府沔县 民许洪才因佃租事伤土著谭仕林身死案 63 17/5 汉中府留坝厅 民史正太因索欠戳伤范老八致死案 64 17/11 延安府宜川县 民魏存德因索欠踢伤魏明经致死案 65 18/1 延安府甘泉县 民冯长元因还房钱事砍伤李敬儿致死案 66 18/9 兴安府安康县 民邱幅起因争种土地谋杀无服族弟身死案 67 18/9 同州府华州 民雷正春因索欠殴伤马文青致死案 68 19/2 汉中府褒城县 民唐文故杀雇主余海并误伤陈正元身死案 69 19/9 鄜州直隶州宜君县 民陈春贵致伤罗英会身死案 70 20/7 凤翔府凤翔县 民史财因工钱事伤岳遂五子身死案 71 20/8 汉中府西乡县 民陈奉因债务伤王长青身死案 72 20/12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蒋银万因债务伤李文典身死案 73 20/12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褚光帼因种地纠纷伤刘胜举身死案 74 21/8 兴安府安康县 民吴坤山等共殴谭贵潮身死案 75 22/6 西安府宁陕厅 民周维太因欠债谋杀王棕贵身死案 76 23/5 汉中府略阳县 民雷洪隆等因索讨割麦工钱殴伤梁奉身死案 77 23/7 延安府甘泉县 民王高科因被追讨工钱殴毙同乡阮五十子案 78 24/4 西安府户县 客民陈贵因索欠殴毙余埋娃子案 79 14/12 西安府三原县 民雒向行因王田氏索欠将妻马氏砍伤致死案 80 15/3 西安府渭南县 民妇李梁氏被张念宗斥骂自尽案 81 15/4 同州府大荔县 田东方子因索欠启衅秽骂孙王氏致氏自缢案 82 15/8 兴安府安康县 民杨银因帮讨利谷扎死邹通案 83 17/2 汉中府略阳县 民王邦富因砍树纠纷砍死房主莫肖氏案 84 21/3 邠州直隶州三水县 郭文智因强嫁堂嫂刘氏被小功堂侄郭更有殴伤身死案 85 13/11 乾州直隶州 李上泰戳伤无服族祖武生李殿奎身死案 86 15/1 兴安府汉阴厅 武生刘镇因被索欠致张登科身死案 87 23/11 延安府延川县 监生高士麟因索欠殴毙胞叔高德案 88 15/2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佃户田因转租纠纷扎死杨先泰案 89 15/4 商州直隶州山阳县 孟怀仓等殴伤无宗胜身死案 90 20/12 延安府葭州 民高文常因地租纠纷伤高庭丰身死案 91 22/12 延安府宜川县 民白志尚因索讨欠租殴毙佃户王裕德案 92 23/8 西安府韩城县 民王玉娃因腾地之争被田主贾钟贤殴伤身死案 93 24/7 凤翔府扶风县 民薛恭沅被讨租之田主巨世栋扎伤身死案 94 9/12 榆林府府谷县 客民郝增先因被疑侵吞事扎伤雇主身死案 95 10/3 凤翔府宝鸡县 民茹徐家娃砍伤雇主杨迎春身死案 96 10/6 乾州直隶州武功县 民赵根子因雇工赵东五懒惰将其殴伤致死案 97 10/11 汉中府留坝厅 民朱耀庭因被讨要工钱踢伤雇工身死案 98 14/4 兴安府安康县 民毛起珑因房租事殴伤傅兴身死案 99 14/5 凤翔府陇州 工头崔太因工钱纠纷致死张荣案 19/5 汉中府宁羌州 民曹文举伤雇主李砚虎身死案 21/9 凤翔府岐山县 民阮元斗因工钱纠纷致伤客民秦芳身死案 21 凤翔府凤翔县 民马九殴伤雇工杜居子身死案 5/7 西安府咸宁县 民班得还等因工钱纠纷伤沙瓜儿身死案 5/11 汉中府西乡县 民袁士秀因口角戳死回民马兴才案 7/5 西安府咸宁县 回民马六一儿等共殴回民马自良身死案 10 西安府咸宁县 民唐继有、唐进礼因回民唐文满强横将其谋杀案 15/11 西安府渭南县 回民禹金庄儿扎伤雇工李二沙身死案 17/8 西安府渭南县 民马洪金等因争食柿子殴伤马庭振致死案 18/5 西安府临潼县 民王明花致伤无服族兄王明周身死案 21/6 同州府大荔县 民于考儿殴死欲赎地之于兴云案 7/2 汉中府南郑县 民赵克起因口角打死嵇居忠案 7/6 汉中府凤县 汤洪升因劝架打死同营兵丁孙喜案 13/11 商州直隶州雒南县 民党一温致死差役李兴才案 14/11 兴安府紫阳县 民妇王黄氏殴伤小功堂侄王玉身死私和匿报案 15/4 凤翔府眉县 梁起幅控告史幅真等侵地赔粮致史幅真自缢案 16 兴安府旬阳县 差役夏友等吓逼禹正文投河身死案 16/3 绥德直隶州米脂县 高理祥因转卖土地纠纷殴伤马万益身死案 16/3 榆林府府谷县 刘均珠因找价绝买纠纷殴伤刘兆业身死案 20/2 同州府韩城县 民刘玉环殴伤胞兄刘玉辰身死贿和私埋案 说明:表中的“年月”栏目中符号“/”前面的数字为嘉庆朝的年序,后面的数字为月份;“府州县”栏目中前面的为府或直隶州,后面的为府州所属的县;“标题”栏目中的内容为《辑刊》原标题去掉所属开头省县地名后的部分;“页数”栏目中序号1-24来自《辑刊》的第一册,序号25-83来自《辑刊》第二册,序号84-来自《辑刊》第三册。 时空范围:嘉庆朝(—)共25年,表中的档案在25年间大体呈均匀分布状态。其中案件最多的是嘉庆十五年16件、嘉庆十六年14件,嘉庆十年和廿一年各8件,其余最多的年份6件,平均每年4.76件。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嘉庆朝陕西省领府7,直隶州5,厅7,州5,县73。府州县包括:西安府,领厅2,州1,县15;同州府,领厅1,州1,县8;凤翔府,领县7,州1;汉中府,领厅3,州1,县8;兴安府,领厅1,县6;延安府,领县10;榆林府,领州1,县4;乾州直隶州,领县2;商州直隶州,领县4;邠州直隶州,领县3;鄜州直隶州,领县3;绥德州直隶州,领县3。 案件分布:表1中的件档案中,西安府21件,同州府14件,凤翔府10件,乾州直隶州2件,邠州直隶州3件,以上为关中地区,合计50件;汉中府22件,兴安府18件,商州直隶州12件,以上为陕南地区,合计52件;延安府7件,榆林府5件,鄜州直隶州4件,绥德直隶州1件,以上为陕北地区,合计17件。这些案件包括了嘉庆朝陕西所有的府州(厅)与直隶州,具有普遍性;尤以陕南的汉中府、兴安府为多,关中的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次之。 基本内容:这些命案当事人的口供中交待了家庭直系亲属的年龄、兄弟数、婚育、职业等基本情况,可了解当时人口、年龄、婚姻、家庭等情况,是认识民众生命周期的基本资料(见表2)。 表2《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陕西籍当事人资料详表 序号 当事人 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 页码 1 李澍修29岁 已故 已故 一兄;女人王氏 训萌度日 4 2 王学武55岁 父故 丁氏 有五弟兄,行二;同居度日 12 3 毛建业25岁 毛起奉 王氏 女人杨氏,生一女 宰猪度日 49 4 刘元林46岁 已故 已故 女人闫氏,生二女 伙开银匠铺度日 53 5 窦景顺42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梁氏,一个女儿 56 6 杨世友34岁 已故 冯氏75岁 弟兄二人;女人冯氏,生一儿,1岁 86 7 杨元喜31岁 已故 已故 兄弟二人,兄卖布; 出家为僧 94 8 杨景文20岁 杨聪礼 继母高氏 祖父祖母均在;同居度日;女人姚氏,生一儿 9 柳学义 柳遇满77岁 女人李氏,生二子 10 卫创升35岁 已故 已故 没女人 11 侣泳强68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死了,生一子 12 杨助清19岁 已故 雒氏46岁 兄弟三人,居长;没娶女人 13 张世魁62岁 已故 已故 女人赵氏,两个儿子 佣工度日 14 傅智丰40岁 傅怀西67岁 郑氏67岁 兄弟二,居长;女人刘氏,没生儿女 15 郭更有21岁 病故 母42岁 兄弟四人;居长 佣工度日 16 赵文科24岁 赵汉 张氏 兄弟四人;娶妻二年,没生儿女 佣工度日 17 李学31岁 已故 张氏58岁 兄弟五,居长;女人张氏,生三子 18 贺惠54岁 已故 高氏 兄弟六,行二;女人薛氏,没生儿子 19 杨范书60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吕氏,两儿子,大儿13岁 种地度日 20 陈九伦47岁 已故 孙氏73岁 兄弟三,行二;同居各爨; 没女人 佣工度日 21 秦邦贵37岁 已故 张氏74岁 女人张氏,一个儿子; 伙种山地 22 刘光彦25岁 已故 封氏58岁 弟兄二,长兄30岁;女人蒋氏,生两儿,大儿子7岁; 种地度日 23 韩登顺34岁 已故 已故 兄弟三,行三;同居度日;女人李氏,生两儿 24 赵金41岁 赵大学64岁 已故 女人张氏,生两儿一女 25 陈来珠25岁 陈海 26 安三友58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司氏,生两儿子;自幼眼瞎 27 胡交年27岁 已故 王氏58岁 弟兄三;女人刘氏,没生儿子 短工度日 28 张庭英27岁 病故 万氏63岁 兄弟三,长兄35岁,行二;女人韩氏,生一儿,年9岁 钱铺生理 29 高仁吉50岁 已故 改嫁 女人张氏,生一儿子 30 高改生27 已故 蔡氏74岁 女人冯氏23岁,生一儿,年4岁 卖柴度日 31 赵德元32 已故 惠氏56岁 弟兄三,居长 开钱铺 32 潘贵玉36 已故 李氏 弟兄二,行二;女人鱼氏,没生儿子 33 王居礼43 已故 改嫁 有一兄;女人王氏,无子 卖布度日 34 周元才45 已故 已故 弟兄五,行五;女人邹氏,生一儿一女 35 张均20 病故 吴氏67岁 无弟兄;女人王氏,没生儿女 36 孙成刚47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女人何氏,没生儿女; 开酒坊 37 崔世元52岁 已故 已故 女人王氏,没生女儿 38 苏文炳23岁 已故 已故 没有弟兄;女人杜氏,没生儿女 39 吴金玉38岁 吴炳潭61岁 陈氏60岁 没有弟兄;女人张氏,生一儿, 开杂货铺 40 秦得荣40岁 已故 已故 无兄弟、妻子 41 李有34岁 李英俊64岁 孙氏62岁 弟兄二,居长;女人权氏,生两儿 伙卖木材 42 张银18岁 张士文58岁 杜氏50岁 弟12岁;女人徐氏,没生子女; 务农度日 43 折金竺28岁 折尔贵56岁 张氏58岁 无兄弟、妻子 佣工度日 44 霍连喜35岁 已故 已故 无兄弟、妻子 伙种山地 45 杨登贵 已故 已故 女人李氏,生一儿,年9岁 46 茹添得55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死,无子女; 稞种度日 47 樊正海36岁 樊荣先 张氏 弟兄三,居长;没娶妻 种地度日 48 廖正坤23岁 廖文章47岁 曾氏48岁 弟兄三,行三;无妻子 佣工度日 49 谈开礼28岁 已故 舒氏70岁 无弟兄;没娶女人 稞种度日 50 郭英63岁 已故 已故 女人赵氏,生一女; 务农度日 51 范占鳌26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居长;没娶女人 裁缝铺 帮工 52 张兴才32岁 已故 已故 女人田氏,生一子; 开饭店 53 郭成积47岁 已故 何氏76岁 无弟兄;妻屈氏,生一儿,年17岁 种地度日 54 余道和57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死,一儿子余世旺 稞种度日 55 李贵32岁 李爱 已故 弟兄二,居长;没娶女人 烧卖木炭 56 宁士成23岁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57 杨魁选66岁 已故 已故 没妻子;锯匠 佣工度日 58 董景瑞45岁 董兰林67岁 牛氏73岁 弟兄三,居长;没女人 垦山佣工 59 王兴顺25岁 王云凤62岁 赵氏57岁 没弟兄、妻子 铜匠度日 60 刘茂魁45岁 已故 朱氏80岁 弟兄四,行三;没女人 纸坊佣工 61 朱三娃26岁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62 许洪才47岁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63 史正太30岁 病故 司氏64岁 无弟兄;女人崔氏,没生儿女 裁缝 64 魏存德42岁 已故 陈氏74岁 无弟兄;女人程氏,两儿,长子22岁,次子15岁 种地度日 65 冯长元52岁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66 邱幅起43岁 在世 在世 一兄,无妻; 伙种山地 67 雷正春22岁 已故 刘氏79岁 兄弟二,居长;妻刘氏,生四女 68 唐文41岁 唐士元 谢氏 无妻子 佣工度日 69 陈春贵31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无妻子 管领戏班 70 史财35岁 史学忠73岁 文氏71岁 无弟兄;女人薛氏,生一儿,年8岁 开纸坊 71 陈奉46岁 已故 余氏73岁 弟兄四,居长;女人许氏,没生儿子 开酒铺 72 蒋银万28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三,行三;女人应氏,生一女 佃种山地 73 褚光帼25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三,行三;没娶女人 佃种 74 吴坤山43岁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木匠 75 周维太34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居小;没娶女人 佣工度日 76 雷洪漋29岁 雷春礼66岁 余氏67岁 女人黄氏,生一女 佣工度日 77 王高科39岁 王合73岁 已故 弟兄二,行二;女人王氏,生一子一女 租种山地 78 陈贵48岁 已故 王氏72岁 无弟兄、妻子 摆杂货摊 79 雒向行44岁 已故 已故 女人马氏,生一儿,年5岁 开纸货铺 80 李之祥 被讨租者辱骂投井而死 种地度日 81 田东方子 32岁 田必要61岁 已故 弟兄三,居长;分居各爨;女人张氏,没生儿子 82 杨银 83 王邦富55岁 已故 已故 没有妻子 佣工度日 84 郭更有儿 21岁 病故 刘氏42岁 弟兄四,居长 佣工度日 85 李上泰40岁 李备 贾氏 弟兄三;女人已故,生子9岁 86 刘镇38岁 刘新鼎80岁 已故 弟兄三,行二;妻许氏,没生儿子 87 高士麟28岁 已故 于氏 弟兄四,行三;妻都氏,生一女 88 田车田41岁 已故 已故 女人邹氏,生两儿 佣工度日 89 孟怀仓31岁 孟成珠68岁 肖氏62岁 有一弟19岁;女人肖氏,生一女 租种度日 90 高文常35岁 高洪年72岁 郭氏67岁 弟兄二,行二;女人李氏,生二儿 91 白志尚55岁 已故 杨氏84岁 无弟兄;妻周氏,生一儿,年12岁 92 贾钟贤35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行二;女人张氏,生一儿 务农度日 93 巨世栋31 巨光舞63岁 杨氏62岁 弟兄二,居长;女人王氏,无儿女 租种山地 94 郝增先34岁 郝兴业58岁 继母35岁 弟31岁;女人张氏,没生子女 开杂货铺 95 茹家娃23岁 茹德年62岁 姬氏59岁 无弟兄、妻子 帮工度日 96 赵根子28岁 赵光助54岁 康氏62岁 一兄;女人漆氏,生一儿,9岁 97 朱耀庭 佣工度日 98 毛起珑50岁 嗣父84岁 已故 女人何氏,生一儿,年6岁 佣工度日 99 崔太36岁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工头 曹文举27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居长;女人杨氏,生一女 卖布帮工 阮元斗37岁 已故 徐氏67岁 弟兄二人;无妻子 纸铺帮工 马九38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李氏,生两儿 开酒馆 班得还42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沙氏,生一儿; 佣工度日 袁士秀35岁 袁仲礼69岁 已故 弟兄三,居长;未娶女人 佣工度日 马成全54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冯氏,生二儿 唐继有46岁 唐文兴62岁 冯氏61岁 弟兄四人;女人米氏,生一儿 禹金庄30岁 病故 全氏54岁 弟兄四,行二;女人李氏,生一女 务农度日 马洪金41岁 病故 马氏67岁 一弟;女人余氏,生一儿 王明花37岁 往口外不归 已故 一兄;女人马氏,生一儿 于考儿24岁 于瞎慢58岁 伍氏60岁 弟兄三,居长;女人丁氏,生一儿 赵克起49岁 已故 已故 弟兄二人;无妻子 赶脚营生 汤洪升37岁 汤连榜69岁 雨氏65岁 弟兄三,行三;女人陈氏,没生儿女 党一温58岁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炉匠 王黄氏55岁 已故 已故 二子均已成家 梁启幅76岁 夏友 差役 高理祥60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栾氏,生三儿 佃种度日 刘均珠32岁 刘相 党氏 弟兄六,行四;女人蔺氏,生一女 刘玉环50岁 已故 已故 女人惠氏,生三儿 佃种度日 任士保34岁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短工度日 杨得34岁 已故 陈氏77岁 弟兄二,行二;女人靳氏,没生子女 醋铺长工 吴秉禄51岁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故,生一儿子 货郎生理 薛寅 已故 已故 卖布度日 说明:1.本表中有22例外籍人的记录,因他们多年在陕西居住生活,多已婚育生子,因此也将其列入本表;2.本表增加了陕西人在外地活动的记录,即-号。3.号命案当事人为女性,其余均为男性。4.本表均来自《辑刊》的一、二、三册。 细读档案制成表2,为我们研究嘉庆朝陕西底层民众的婚姻家庭、生育年龄、生育子女数、男女寿命等情况提供了样本资料。 (1)男性的独身未婚情况。在有明确记录“没有女人”或“无妻子”的33件档案中:20岁以下未婚的1人(12号19岁);20岁年龄段的9人(43号28岁、48号23岁、49号28岁、51号26岁、56号23岁、59号25岁、61号26岁、73号25岁、95号23岁);30年龄段的10人(10号35岁、44号35岁、47号36岁、55号32岁、69号31岁、75号34岁、99号36岁、号37岁、号35岁、号34岁);40年龄段的10人(20号47岁、40号40岁、58号45岁、60号45岁、62号47岁、66号43岁、68号41岁、74号43岁、78号48岁、号49岁);50年龄段3人(65号52岁、83号55岁、号58岁);60年龄段1人(57号66岁)。不排除存在离婚的情况。王跃生以25岁以上作为清中叶男性晚婚的年龄划分,以45岁以上做为不婚的年龄划分。据此可知,在25—45岁之间的晚婚者有22例,占未婚年龄人数的三分之二强。这说明清中叶陕西男性存在晚婚情况,有相当一批壮年未娶的男性群体存在。尽管这批青壮年男性有可能在之后结束独身而组建家庭,但仍是晚婚晚育的主体。45岁(含)以上者10例,占未婚者的三分之一弱。这批男性已丧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机会,成为终身不婚者。 (2)在当事人父母均有明确年龄记载的19件档案,可获知案发当事人父母的婚姻年龄差。其中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12例,年龄差最大者23岁(如94号);小于女性的6例,年龄差最小1岁,最大8岁(如96号)。据王跃生以乾隆朝刑科题本研究18世纪中后期中国婚姻家庭的结论,丈夫年龄大于妻子5岁以上者占有较高的比例,黄土高原区婚姻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比例,以及婚姻中男性大于女性10岁以上的比例高于全国水平,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陕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除男性大于女性之外,还存在女性大于男性的情况,说明男女婚龄差具有同步性。这也与男性晚婚并处于不利地位有关,符合这一结论。 (3)在当事人发生命案时有明确的年龄记载、同时父亲或母亲健在且有明确年龄记载的68件档案(其中有父亲者25件,有母亲者43件),可藉此分别考察当事人父母亲的生育年龄,进而推算当时陕普通男女婚育年龄与生育情况。 在有父亲明确年龄记载的档案中,长子与父亲的年龄差即可推算出父亲的生子年龄。父亲20岁年龄段生子的8例(14号27岁、24号23岁、39号23岁、43号28岁、48号24岁、58号22岁、81号29岁、94号24岁);30岁年龄段生子的14例(41号30岁、59号37岁、70号38岁、76号37岁、77号34岁、89号37岁、90号37岁、93号32岁、95号39岁、96号34岁、98号34岁、号34岁、号34岁、号32岁);40岁年龄段生子的2例(42号40岁、86号42岁)。在多子家庭中,非长子的情况也多有存在,如90号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37岁生他,意味着其父亲至少在37岁已经婚育;类似情况还有86号。除此,还存在早婚早育情况,如号16岁生子,28号18岁生子。这说明清中叶陕西男性多在30岁生育得子,少部分存在早婚早育情况。 利用有母亲明确年龄记载的档案,可推算出陕西底层女性的生育年龄。20岁年龄段生育的有17例(12号27岁、14号27岁、17号27岁、20号26岁、31号24岁、39号22岁、41号28岁、48号25岁、53号29岁、58号28岁、71号27岁、78号24岁、84号21岁、91号29岁、号24岁、号26岁、号28岁);30岁年龄段生育的有19例(21号37岁、22号33岁、27号31岁、28号36岁、42号32岁、43号30岁、59号32岁、60号35岁、63号34岁、64号32岁、70号36岁、76号38岁、89号31岁、90号32岁、93号31岁、95号36岁、96号34岁、号30岁、号36岁);40岁年龄段生育的5例(6号41岁、30号47岁、35号47岁、49号42岁、号43岁);50岁年龄段生育的1例(67号长子,母亲57岁生育);早婚早育的1例(号15岁),可知清中叶陕西普通女性生育的平均年龄为31岁。 在多子家庭中,女性生育较早且生育子女较多,说明生育周期较长,女性寿命也相应长于男性。在命案发生时父母均健在者25例;多数情况是父亲已故而母亲健在;而在有母亲确切年龄记载的44例档案中,除94号与继母年龄相仿外,其余的43例中,80岁以上者1例(60号80岁);70岁年龄段者13例(6号75岁、20号73岁、21号74岁、30号74岁、49号70岁、53号76岁、58号73岁、64号74岁、67号79岁、70号71岁、71号73岁、78号72岁、号77岁);60岁年龄段的16例(14号67岁、28号63岁、35号67岁、39号60岁、41号62岁、63号64岁、76号67岁、89号62岁、90号67岁、93号62岁、96号62岁、号67岁、号61岁、号67岁、号60岁、号65岁)。这说明陕西女性的寿命在60-70岁之间当是普遍现象。 (4)生育子女数情况。当事人的弟兄数反映父辈的生育及家庭规模,而当事人的婚育状况也可藉此知晓,由此可知当事人两代家庭的生育状况与家庭规模。统计资料得知,父辈只生育当事人一人的有63例,生育二人的30例,生育三人的17例,弟兄四人的8例;弟兄五人的3例;弟兄六人的2例。可知,当事人父辈生育子女一人的占二分之一强,生育二人的占四分之一弱。 当事人自身的婚育状况中,除33例未婚、12例婚育状况不明外,已婚者77例。其中已婚未育者22例(2号、14号、16号、18号、27号、32号、33号、35号、36号、37号、38号、42号、46号、63号、71号、81号、82号、86号、93号、94号、号、号),也即档案中经常出现的“女人过门多年,并没生子女”的情况,说明当时已婚夫妇在婚后并非立即生育或较晚生育。根据乾隆朝档案供词,当事人婚后一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生育行为者为极少数,婚后5年左右或5年以上生育或未生育者占一定数量,婚后10年以上未生育者则与夫妇生理障碍有关。已生育者55例中,生一子者35例,生二子者15例,生三子者4例,生四子者1例。可知当事人生育一人者占二分之一强,生育二人者占三分之一弱。这与其父辈的生育情况颇为相似。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代际间有着相似的生育情况,决定其子女人数与家庭规模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有学者研究小农家庭,认为通常家庭只包括二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尤其在耕作之家,因地亩数的限制,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在子女未婚嫁之前很少超过五六口以上者。通过对当事人父辈及自身的生育情况的统计,发现清中叶陕西民众生育一子为普遍现象,生二子也占有一定比例,这意味着一般小农家庭的人口规模在3-5人;子女婚嫁分居各爨后,家庭人口规模实际上还要减少。这与前引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须注意的是,由于内科刑科题本在记述当事人家庭成员及自身的婚育子女数时,多以有几个“弟兄”或自身“生儿子”或“没生儿子”的形式呈现,所以一般记述有几个弟兄、有几子,多是指男性成员。在记录无儿有女的情况时,则明确记述“生女儿”。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姊妹”和“女儿”在作为同辈或子女数时因被主动隐去而成为家庭中的潜藏人口。这说明存在现实的家庭人口要比当事人所供述的要多的可能。 同居情况。在独自家庭,父母与儿子往往同居共爨。在多子家庭,父母往往与已婚儿子分居各爨,而且大多时候与长子同居,是为“长子不离祖庄”风俗。多子家庭分居时,若有儿子未婚,父母多与未婚儿子同居。如8号咸阳县当事人杨景文与兄杨景科同居度日,均已婚生子。祖父生父亲一人,故并未分家,祖孙四代同居一院。祖父、祖母、父亲、继母均在。平日家事由祖父经管。兄杨景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时常偷窃家里银钱、粮食花销,祖父、父亲屡教不改。其兄偷藏一袋麦子欲变卖还赌债,被弟杨景元发现并告发于祖父、父亲。一日祖父、父亲均不在家,其兄醉酒后“拿面刀”伺机报复;杨景元“心想哥子自己不成人反要合小的拼命,祖父年纪老了,父亲为人软弱管他不下,小的日后必定受他的害,起意把他打死。”87号当事人兄弟四人分居各爨,因讨要分家时父亲将胞叔所欠分给自己,屡向胞叔讨要不得,引发争斗致死胞叔。可见,多子家庭分家析产时,财产、债务也会被分配。 过继情况。过继,亦称继嗣、承嗣,指已婚无子女者以兄弟﹑堂兄弟等同宗人之子为自己之子,以维持祭祀或作为继承人以继承财产的做法。一般多以同宗族内的男性为主,以维系家庭,延续宗脉,继承资财。作为古代社会一种附着于宗族制度的亲属关系及收养制度,曾普遍流行于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民间基础与社会影响。过继现象也较多地出现在清中叶的陕西民间社会,且往往因为宗族内的经济纠纷,尤其是宗族内的产业继承问题而引发命案。这样的案例有9例。如1号当事人李澍修自幼过继给族叔李光启为嗣,磨面生理。其缌麻服兄李瑞征因屡次向其借钱未果,欲打他出气,却被李澍修殴伤致死。2号王学武因耕种过继而来的族叔王涺的稻地,后王涺被土匪所害,王涺的胞弟王淮据此向王学武讨收稞租,王学武以“王涺已经过继另过”,“与他无干”为由拒绝,由此引发争执,打斗中扎伤致死王淮。11号当事人侣泳强的无服族叔侣彦实无子,抱养井表为义子,改姓侣,生侣永幅。侣彦实死后,侣表作为义子将义父旱地当与人耕种,便携子侣永幅在他县生活廿余年;回来后要绝卖义父产业,侣泳强以“从未回乡祭扫”和“忘了根本”为由,斥其不该绝卖,因而争执,打斗中将侣永幅殴伤致死。官府对此案的判决,也与侣泳强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与裁决宗族财产纠纷时,往往持维护本宗利益的立场。12号当事人杨助清为索分钱财扎伤无服族兄杨锐致其死亡,起因族长杨某因年老无嗣,要族侄杨锐照料(实际是以杨锐为养子,便将地亩卖得的银钱分予杨锐);杨助清心想同是侄子,分钱与杨锐而不与自己,心中不服,便向杨锐要求均分;杨锐不肯,彼此吵骂,打斗中杨助清将杨锐刺死。可知,承嗣人、嗣子或养子,往往具有优先继承被继嗣者财产的权力,同时也要履行为被承嗣者养老送终的义务;同时,族内的其他成员的继承权则沦为次要,若生分歧,往往酿成命案,18号便是例证。18号当事人李学,其祖父四兄弟,长房无嗣有绝业,二伯自幼过继他人,原先由三伯耕种的长房产业卖与李学的祖父;李学祖父死后,三伯之孙李荣便要分绝业,打斗中李学打死李荣。类似情况还有23号、32号、67号。这说明当时家族、亲戚之间过继是常有的现象,过继者不仅在原宗难以享有宗族财产的继承权,而且在承嗣方也难以顺利继承财产,因此往往因产权归属与继承权而引发争斗和命案。此外,还存在自由过继给(其实是被收养)外省人的情况,如30号。 父母的赡养问题。在独子家庭,父母多与子女同居,赡养多由独子承担。如前述30号案发当事人为养子,独自赡养母亲;49号谈某是家中独子,“篾匠营生”,“时常寄银回家养母”;63号渭南人史正太寄居长安县,裁缝生理,“常寄银钱养活母亲”。而在多子家庭,多由诸子轮流赡养。如20号韩城县人陈九伦,年47岁,无妻子,佣工度日,生父母均故,继母孙氏,年73岁,弟兄三人同居各爨,“继母由弟兄三人轮流供赡”。 二、“生理”中的生计格局前近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资源品类、地理区位等直接决定区域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同时对人们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与活动范围也产生直接影响。陕西生态类型多样,是中国自然类型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旱寒的陕北黄土高原、温润的关中冲积平原、湿热的陕南秦岭巴山地,构成陕西三大地理单元。受此影响,形成各具特色的陕北、关中、陕南不同的地域文化与生活形态。我们虽不能直接知晓清中叶陕西民众社会关系的具体情形,但从刑科题本中标记的当事人的“生理”业态及其社会活动,并与地方志进对比互证,则为我们进行合理的综合与提炼提供了样本基础。 在有明确标记“生理”的77例案件中,其中:“种地生理”者(题本中多出现“种地”、“务农”、“伙种”、“租种”、“佃种”、“稞种”等形式)共计22例(19号、42号、47号、50号、53号、64号、80号、92号、号、21号、44号、66号、58号、89号、93号、72号、73号、号、号、46号、49号、54号),其中陕南12件,关中7件,陕北3件。“佣工生理”者(包括“短工”、“帮工”、“帮伙”等)共计23例(13号、15号、16号、20号、27号、43号、48号、56号、57号、62号、65号、68号、76号、75号、83号、84号、88号、98号、95号、99号、号、号、号),这其中陕南11件,关中9件,陕北3件。可知陕南与关中地区的民众业态多以种地与佣工为主。其他“生理”大多为商业或手工业者,如卖布(94号、33号、61号、号、号)、杂货铺(39号、78号、94号、37号、63号)、纸坊(60号、70号、79号、号)、裁缝铺(41号、51号、63号)、卖柴(30号)、炉匠(号)、铜匠(57号)、钱铺(31号)、银匠(4号)、篾匠(49号)等多集中在陕南山林地区与关中地区。 结合表1、表2,可总结出清中期陕西底层民众多以种地、佣工为主要业态,陕南地区尤为明显,手工业较为活跃,还较多涉及与外籍“客民”的关系的记载。如在题本命案中涉及外籍移民者23例,其中山西4人(39号、65号、77号、94号)、四川7人(40号、47号、48号、55号、57号、68号、号)、湖北4人(22号、49号、54号、号)、湖南3人(51号、56号、66号)、安徽1人(72号)、河南1人(46号)、甘肃1人(62号)、贵州1人(号)、湖广1人(76号)。这些外籍客民除山西籍多分布在陕北的延安府、榆林府,且主要以开杂货铺居多外,其余悉数分布于陕南的汉中府、兴安府,也多以租种、佣工居多。这与陕南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地关系以及清政府推动的移民开发等因素不无关系。 这一现象在同时期的在地方志中也多有佐证。如乾隆年间镇安县“迩年来湖北人来迁者日众,善于修治日工,里民转相觅食,四乡景色渐觉改观。”嘉道年间长期任职汉中知县的严如熤就指出:“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如宁陕厅“川楚各省民人源源而来,以附其籍。有资本者买地、典地,广辟山场;无资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课生。统计烟户,大约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南、两广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最少者山东、直隶、浙江、甘肃数省耳”,形成“楚民善开水田”、“蜀民善开山地”的局面,宁羌州还出现“俗兼南北,音杂秦蜀”的格局。 移民佃种土著的荒地(山),以租种、佃种、伙种、稞种等形式成为佃户,或者成为纸厂、铁厂、耳厂的雇(帮)工,构成陕南主要的移民佃农与雇工群体。频繁的土地租种与手工业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利益纠葛也随之多发。“农服田力穑,然山坡荒地事倍功半,民苦徴徭,招佃代种,少收租钱,以应差派。无恒产者佣工食力而已。”在土地租佃过程中,出现了移民即是地主也是雇主,租户即是佣工也是帮伙的情形,甚至出现多次承租、转租后雇主变为地主的现象,因而产生以讨要地租、索要工钱,或因土地转卖、转租等引发的命案,反映出人际关系多围绕土地耕种、地租缴纳、工钱索讨等鲜明特点。如72、82、89号案件便是典型的因同一山地被多家外籍租户承租,最后引发多方纠缠打斗致人死亡的命案。不惟陕南,这种多方承租引发命案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地区。如50号陕北宜君县周某将芦苇地多次转当,从中赚取差价,引发承租者之间争斗而致人死亡。这些案件均说明在民众租种土地时,因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而导致的权利不清、利益模糊、多方纠葛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土著之间、土著与移民、移民与移民之间发命案频发的重要原因。 再者,这一方面反映出陕南土地租佃关系的发达与复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中叶陕西基层社会的法制生态。这种现象也被地方志佐证。如“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率多争佃距压或因辗转佃种,以致兴词控告者几无虚日。”汉中知县严如熤就认为,“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地不能抗争,间有控讼到案”。此外,外籍客民在促进陕南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复杂。如西乡县“山内有纸厂三十八座,耳厂十八处,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聚五方”,“又有铁厂十七处,柴厂十三处,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这些外籍客民“酗酒、打架、赌博、窃盗者,无处无之”,“每有以微嫌遂成大案”。这清楚地反映出民众业态对社会关系与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 除因争种土地命案外,另一类多发命案则是由“索欠事件”引发的命案。这类命案多发生于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中,且多有如下特点:一是一方推脱求缓,另一方则多立逼全还,遂致命案发生;如44号、57号、68号、74号、77号,78号、85号、号;二是当众讨要前欠有伤颜面,引发打斗至命案;如14号三水县人傅智丰在街上向无服族弟讨要前欠,族弟“斥说小的不该当众讨账”而伤及颜面,叫骂回骂及打斗中将族弟打死。三是讨要前欠的言语冲突中“辱及父母”或“先人”,引发命案;如25号陈来存儿之父与仲世明同为关帝会会首,陈拖欠会费,陈父死后仲讨前欠,仲叫骂中“辱及(陈)父母”,陈姓弟兄们遂将仲打死。四是“无主仆之分”的主雇之间因任务分配不均而打斗后致人死亡;如27号胡交年子受雇于宋起德帮做庄稼,每年工钱七十文,“平日亲戚称呼,同坐共食,无主仆之分”,胡因两次进山背煤炭将肩压伤不愿再去,因之与雇主争执,用炕边石灯柱将宋致伤不治。五是主雇之间因同性情感纠纷而引发的命案;如95号宝鸡人茹某受雇于邻村杨迎春,杨许给茹以资本生理将茹鸡奸,后茹见杨不给资本,便要辞工,杨不依,彼此詈骂打斗,茹将杨砍死。须注意的是,题本中的雇主与佣工之间大多“平日同坐共食,你我相称,没有主仆之分”,并未“立约议息”或“没立明契”,属于大清律例中所谓的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倩工作之平民”,“虽议有年限工价,并非服役,彼此无良贱之分”。这也印证了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借贷双方对借期多不甚明朗对待。雇佣关系的不明确与借贷期限的模糊往往成为索欠类命案的关键。在无利息或利息较低的72例索欠命案中(包括地主与佃农、雇主与雇工、贷方与借方),债权人(贷方)打死债务人(借方)42例,债务人打死债权人30例。这也印证有关学者“在零利率的情况下,借方打死贷方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贷方打死借方的比例”的研究结论。 男女两性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科题本中也多有女性被害或因被秽骂而自杀的记载。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价值的界定与肯认,主要集中于文化、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领域,而非经济生产领域。对女性的贞操是极为看中的,在对女性的侮辱中,“最普通的侮辱形式是质疑女人的贞操。这种侮辱特别普遍,而且效果非常明显。”这对男女的性心理、性别意识与社会行为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女性一旦涉及经济纠纷,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丈夫因其他男性中伤妻子的忠贞品行而疑心妻子不忠,遂引发命案;如9号合阳县柳学义有牛一头,托族叔柳遇一代牧,柳遇一欠钱于王某,王某索讨前欠,便要拉牛作抵,柳学义上前阻拦,王某以“看柳学义不像有牛之人”,斥骂“除非伊妻养汉挣来”;后柳学义“忆及牛只本系妻用钱置买”,心疑王某骂出有因,恐有奸情;后拉妻前去与王某对质,其妻不从,斥责柳“混听人言污其名节,坐地泼闹”,“声言殴毙亦不前往”;柳学义“疑奸情是实”,遂将妻子勒死用骡移尸王某窑前,冀以尸诬赖。二是女性当事人因不堪男性对自己品行的质疑或辱骂而自尽;如81号大荔县田某替弟弟向孙某讨要前欠,田骂到“今日如不还银,着伊女人陪我睡觉顶账”,孙妻王氏听闻后因“被秽辱不能做人”上吊自尽;再如80号渭南县李之祥欠张某地租,张某讨要时李某恰不在家,李母如实相告,张某不依而与李母吵嚷,并骂李母“老泼妇”;李母“气忿不过”,“拾取瓷片在自己头上乱划”;张某又声言告官,李母说“我与你拼命”后跳井而亡。而官方对此类命案的处置,尤其对启衅秽骂妇女者(如对9号案中的王某、对81号案中的田某),均以“因他事与妇女口角、詈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责安置”来处理,显示出清代司法制度对女性贞节观念的维护要超过对女性生命权本身的维护的特殊情况。还有第三种少见的情况,即丈夫不堪妻子羞辱而将妻子杀死的案例。如79号雒向行“开纸货铺生理”,因生意折本,未能偿还借欠,被债主搬去店内纸张货物,妻子埋怨其“平日不该好酒,把生意做坏”,“有何脸面还要喝酒,不如快死了的干净”;雒被骂气忿,顺取桌上菜刀将妻砍死。 须注意的是,妇女放高利贷实属罕见。如82号寡妇杨邹氏放贷与夫弟,因夫弟未及时将本息一并还清,遂叫来母家侄儿二人到夫弟家索讨,打斗中夫弟之子将杨邹氏一侄子刺死。号也是如此,不过是唯一一例女性将男性打死的命案。此类命案中,女性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角色,反映出传统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的不对等。 三、“生理”中的生活样态(一)衣着材质与布匹贸易 在刑科题本中,出现“卖布生理”者6例(7号、33号、61号、94号、号、号),而且这些因布匹贸易而引发的命案分布于全省,足见布料已成清中叶陕西民众主要的衣着材质。有学者研究,乾隆后期棉花得以推广,蚕桑业开始枯萎,嘉道年间棉花已完全取代桑而成为关中与陕南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其种由外蕃入于关陕,西安府境多有之,土人织纺为业”;“春种秋收,黄花白子,子成蒙茸吐出,收时最难,可纺为布,其子(籽)可柞油……其种尤多”。如长安县“城市衣履,大半布素”;同官县民“衣多素布”。到道光年间,大荔县“妇女棉二斤可得线三十两,织之可成布三丈余……故四五口之家,可终岁不买布而着衣不尽”。不仅说明当时棉花种植范围较广,加工技术业已普及,而且棉布已成为民众日常衣着的主要衣料,棉布的市场需求较大,因而多有以卖布作为“生理”者。 受生态环境的制约,陕北地区民众的日常衣着则呈现“少布匹而多皮裘”的地域特点。延安府延长县因“棉花不种”,“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蓝大布,率同自州驮来。各地梭布,又皆自晋之平绛购以成衣。”民间还用麻“积做绳索或成稀眼口袋。”延长县养羊普遍,因“布不能做线,毋论暖寒,农民多着黑羊皮袄,本地产剥者,日用为衣,夜可抵被”。在每年四、九月“刮剪绒毛两次”,或“聚则鬻之”,或“觅匠弹绒作帽”,或“合线织毯为腰带”。马、驴、骡等皮革则多作靴、包、口袋等日用器具;富裕家庭还“以狐皮制帽”,“以豻皮制坐垫”,“以狼皮镶褥作套衣马褂。”榆林府府谷县民“多服无布面皮裘。”“安定(县)羊毛为土产,惜无教织者;遍地旱寒,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商贾多山西人。”葭州“土不组织,市中布匹悉贩之晋地。”方志中陕北民众“服”及其来源的记载,不仅明确说明陕北民众的衣着结构,而且还说明山西人的布料贸易已颇具规模,也印证了有关学者关于山西人多在陕西等地经商的研究结论。 (二)作物种植与饮食构成 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包谷见于陕西各地,尤以关中与陕南地区为多。玉米、稻、麦等粮食作物是陕西民众日常的主食来源,因而常以实物租或借贷形式出现在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如17号赵某因邻地雇工种包谷时认错地界而将自家地亩占种,争骂打斗中失手打死自己女人。75号宁陕厅周维谷借王某包谷九斗,后又以麦四斗、做短工还欠,仍有余欠,后无法忍受周的高利盘剥,起意将周杀死。49号、54号、88号均在陕南以“稞种山地”度日,以包谷作为“租纳”,并立有“稞约”,后因欠租无力偿还,引发争骂打斗致人死亡。前引82号寡妇杨邹氏放贷给夫弟,并议“每年出利息包谷二石”。可知,在清中叶的陕西,包谷作为民间租佃经济的实物地租或借贷利息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除了包谷外,刑科题本中还经常出现的粮食作物有麦,如84号邠州郭文智强嫁堂嫂并收取麦六斗作为彩礼;还有荞麦,如15号商州郭更有儿的族叔长期向其“索借粮食”,最多一次“荞麦六斗,从没还过。”其他粮食如谷子、大麦、高粱等在题本也多有出现。 包谷、麦、稻、粟等成为陕西民众主食而广为种植,这也在方志中也有印证。包谷,即玉米,约在明嘉靖年间一路由西北陆路传入陕甘等省,一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到清中叶,玉米在陕西已普遍种植,成为陕西民众皆种皆食的作物。小麦、稻则也是关中民众的主食作物。“小麦出关中者为上品”,且品种分为黑芒麦、和尚麦、御麦三种。其他谷类,如稷“关中处处有之”,“大率黏与不黏两种,黏者酿酒,不黏者炊饭”;粱、大麦、荞麦,皆“可备诸谷之不熟。”此外,清代陕西稻作种植由明代的24县扩大到59县,增加了35县。这说明稻作已在全省大多数地区得以种植。如36号关中的咸宁县人孙伯让将稻地卖与邻人孙某,孙某余欠久未还清,讨欠打斗引发命案。韩城县“以饶水,故裕稻……以域狭,故粟麦独缺”,形成稻、棉、麦、谷兼种局面,以致于“妇欢于室者,谓韩为‘小江南’。”93号韩城人贾钟贤要收回租地,因租户所种“稻黍未熟”不肯交还,贾遂“把未熟稻黍割除,翻地种了麦子”,引发打斗致死租户。可见稻、麦在韩城轮作种植。扶风县“五谷皆宜”,“稻田仅附渭滨,近则瘠地,皆种包谷”。蒲城县局部也种植水稻。陕北的中部县有种植包谷的记载。可见玉米、稻、麦确已为关中民众的主食。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区,海拔较高,常年降水稀少,光照强烈,昼夜温差大,致使地表植物生长周期长,耐寒抗旱,适应性较强,盛行种植小米。受此影响,陕北饮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如延长县“民间日食非一色,或三四顿。晨起多熬小米稀饭,伴高粱米食之;午间或蒸黄米饶馍,打面饼,或绿豆煮汤,豌豆碾面,伴杂粮各菜为磨馍;下午多食小米干饭,或面、或以荍面作呵捞,大都水煮连汤食。喝多不须茶味解渴;亦有山西石楼人常驮鬻于此,皆湖茶。”同时“佐饭肉食多用羊”,且“城乡率喂猪出鬻,除敬神外,不轻宰杀”;此外,民“多不种菜”,饮食“少蔬圃”,“瓜菜鲜食”。府谷县民“不甚饮茶,尚黄软米、羊肉。”其他谷类如糜子、小麦、大麦、荞麦、高粱、燕麦等在地方志中所见多有,也是陕北民众常见的食物。这则难得的记载,不仅说明陕北民众一日的饮食次数、食物构成,还说明山西商人在陕北民众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陕南的秦巴山区,气候湿润,雨量充足,地形多以盆地、山地、丘陵为主,因之影响作物构成与民众的饮食结构,呈现较为明显的多样性。如兴安府石泉县,“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包谷高至一丈许,一株常二三包。上收之岁,一包结实千粒,中岁每包亦五六百粒,种一收千,其利甚大。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小二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可见,玉米在清中叶已成为陕南民众的主食,也说明四川与湖北籍客民对陕南山地开发与作物引进的贡献。此外,马铃薯“乾隆时知食者甚少,嘉庆时渐多,近则偏高山冷处咸漪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资此养生”。陕南“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耕耘,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如旬阳县民在山坡高峻之地种包谷,“山麓平衍,水势迂回”,“山势颇平”处“五谷皆宜,而稻田十居其二”,在山地极寒处则“多种洋芋糊口”。可知清中叶陕南民众已形成以稻、玉米、粟、马铃薯等作物为主的饮食结构。 (三)自然环境与起居形态 题本中陕西不同区域民众的居住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陕西南北差异较大,关中与陕北具有相似性,皆以瓦房与土窑为主。同时,民间居窑卧炕,是陕北与关中地区日常的居住形态与普遍的家居模式。如43号陕北怀远县案发见证人供称,“在后窑听得刘文裕在前窑向折金竺讨要欠钱”,折央缓,刘不依,骂“骗赖”,在窑内打斗中,折顺手拿起炕边镢头将刘打倒不治而亡。如9号、27号、77号、88号、96号、号、号、号等命案题本中多出现窑、炕,命案也均发生于窑内或炕边。这说明命案发生的场地多在家庭生活的居所中,生活用具或农具往往成为案发时最主要的凶器,命案发生多是随机性的。 这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印证。如关中同官县“屋宇质陋,绅富置瓦房,村间多即土穴居,名曰土窑”。陕北宜川县“庐舍不过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村落率多窑居”。安定县“居住多土窑,间有以砖石砌窑者”。榆林县“民间多住窑房”;葭州“民多窑居”;延长县“统计十里村落,房屋居十之六七,石、土二窑居十之三四。住房上三间,外加夏屋,左右为翼室,随基为构,不拘间数。对面用陪厅为客者室,通邑不多;家周宅砌墙火砖,镶土石为上;其次惟石,以泥涂附,上盖土瓦,间用石板镶之。窑居取坚稳美观者,用灰饬,余皆本色。凡窑必筑炕,饮食卧起俱焉……冬暖夏凉,不虞火灾。”这则记载将窑的布局、构造及优点作了清楚的交代。可见,居住瓦房或土窑已成为小农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之一。 陕南秦巴山地多雨湿热,民间起居多用陶器,民居多以瓦房、草棚为主。如98号安康县毛起珑租王某瓦房二间,开茶铺生理;茶铺帮伙傅兴私自挪用并花销房租,被毛得知后与之争骂打斗,将其致死。13号当事人张世魁的堂侄因外出佣工,将“住屋草棚”托其照管,后草棚被雨淋塌,堂侄便要其盖还,张不依,嚷骂打斗中将堂侄打死。陕南题本中的瓦房、草棚居处的租赁不仅成为命案的诱因,还是案发现场。这说明瓦房、草棚等已是陕南普遍的居住环境。这在陕南地方志中也多有印证。如山阳县“城郭市镇外,村庄之历年久远者,尤多用瓦瓮;若沿山傍谷,大半编茅为屋,缀板为墙,无所取于陶;家计稍裕则易之以木”,“以竹代瓦”,谓之“板屋”;且“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此种起居形态在陕南地方志中所见多有。 (四)交通方式及地域特点 行走短途主要是徒步、骡、牛等,长途则骑马。如凤县民众“其用服牛乘马,其畜狗彘鸡豚,贵用物而不贵易物”,“木炭取自南山。”不仅说明平日交通所用畜力,日常肉食,木炭来源均可得知。再如前引9号。此外,马也较为常见的长途代步工具,如94号郝增先在山西人所开的货铺帮伙度日,“骑了马匹去各处讨账”,因怜悯其中一家穷苦,本应讨粟四斗八升而只讨三石,在途中喂马又用去一斗,因而被雇主怀疑私自侵吞,辱骂“伤及父母”,郝遂顺手拿起桌上小刀将山西雇主刺死。 (五)日常用具及其来源 杂货铺,多是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店铺,因其日用性、多样性与便利性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必需之所。如前引94号榆林府的郝增先便在山西人所开的杂货铺里帮伙;39号山西人吴某在商州开杂货铺生理,因买油赊欠,求缓不依,嚷骂打斗中将油铺主吴某打死。78号陈贵摆杂货摊生理,雇佣余某帮做生意,“平日同坐共食,没有主仆之分”,后因余某借钱未还,陈骂他“骗赖”,打斗中致死余某。虽不能详尽知晓杂货铺所卖何物,但刑科题本中多有开杂货铺生理者,或在杂货铺佣工的记载,说明杂货铺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市场。而通过地方志中对民间日常用具的记载,可弥补我们对杂货铺在民间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认知。 关中长安县民用“器惟瓦瓷”。陕北延长县地方志有则难得的关于常用器物的记载:“除祭祀及笔砚纸墨称四宝外,家具厅有椅桌、小凳;房有板床、花柜、炕桌、方箱、衣架、书架、妇女镜架、天平、箅子架、炭炉架、酒床、篮筐、簸箕、柳斗溜子、钱披、梨身木耙、掀板、扁挑、鞭杆,皆竹木属,竹自西安来,木产本地;钟声磬音,炉、铃、?、锄、镰、斧、铧、钩、鎚、锥、钳、钉,为铁属,出自山西河津及永宁。神炉、蜡台、堂灯、火锅、酒壶、饭镟、盆罍为锡属,锡与匠具出山西。……瓶、甑、缸、坛、甕、罐、碗、盘、杯、盏为瓦,瓷属,出山西及瓦窑堡。”清涧县常用器具如“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具),俱盼外省匠作,倍趁其钱……商贾率多晋人。”这些器具从起居日用到生产工具,几乎囊括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器物种类,尤其是金属农具均出自晋商,足见晋商在陕北民众贸易生活中的商业地位,甚至是影响陕北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群体。 余论“社会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以往有关群体、个人的研究,受宏大叙事范式的影响,鲜有从个体的日常生活、人生经历、生命形态与情绪感受的角度考察个人生命、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与意义,这对于全面认识历史中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以及个体的生命与生活无遗是有缺憾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则使研究主体做为活生生的人而得以呈现,使其脾气秉性、喜怒哀乐、人际交往、社会关系、人生历程、生命轨迹等更趋鲜活,成为血肉饱满、个性明显、具有灵动生命与情感体验的人。这在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命与生活的同时,还可窥见个体生命更多的历史细节,避免个体在宏大叙事结构中成为模糊不清、形象不彰的冷漠存在。刑科题本正是在此意义上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与研究视角,使民众乃至个体的生命、生计与生活得到丰满、生动地呈现,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与生动的统一。 刑科题本是地方政府就命案审理向中央上报的案件详情,属于国家司法程序中的规定性文本,具有真实性、可信性、规范性与完整性,同时也蕴含着基层社会丰富的社会生活史内容。而方志多是在时任官员或士绅的主持下,以特定时空中民众的生活实践作为基本背景记述的基层文本,内容更贴近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况。故而,对二者进行对比与互证性研究,无论从资料来源还是方法论上来看,不仅是一种新颖、可行、可信的研究路径,还有助于重建特定时空环境下普通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甚至生态等的整体性的历史样态。本文即着眼于此。但相较日常生活史丰富的研究内容、崭新的研究视角与微观的检视方法来说,本文只是从婚姻、家庭、生命、生计与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应限囿于以往城市中的有识阶层,也不应局限于有识人群的共性,还应重视不同地域中的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也不应仅仅描绘日常生活的静态图景,还更应重视共时性的地域特征与历时性的时代变迁。这当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趋向。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anxizx.com/xxys/10635.html
- 上一篇文章: 国网陕西建设公司年春节期间疫情防
- 下一篇文章: 宋宁刚丨葳蕤的生长评判的可能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