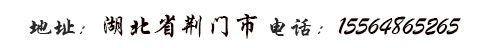杜传坤中国现代幼儿文学的发生
|
作者简介 杜传坤,山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与儿童文学。出版《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等专著,在《人民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前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部分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研究成果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摘要:现代幼儿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建立在成人/儿童、儿童/幼儿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具有双重的“异质性”。中国现代幼儿文学的发生是一个过程,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从独立走向繁荣,可从三个方面考察其源流与萌发:一是古代民间文学的听赏特点与幼儿天然地亲近,蒙学读物中的韵语也与此一脉相承,听赏阅读不应被视觉化或视听结合的图像化阅读所取代。二是晚清以降新式启蒙教育尤其幼稚教育为幼儿文学提供了契机,同时也赋予其较强的教化色彩,而以心理学上的年龄阶段特征作为幼儿文学的理论基础,其适用性以及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关系摆置始终是个问题。三是近现代儿童报刊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为幼儿文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却也可能造成商业化与文学性之间的矛盾。梳理与反思现代幼儿文学的源流与萌发,对当今幼儿文学的发展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现代幼儿文学;民间文学;蒙学教材;幼稚教育;儿童报刊;儿童文学 如果幼儿文学的定义是以满足幼儿的兴趣、想象力,以带给幼儿乐趣、美感为目的的文学,那么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可以被称为幼儿文学的东西。近现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幼儿既不是“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预备”,也不同于年长儿童,幼儿被认为有其独特的兴趣和需求,应该予以尊重和满足,其中包括文学阅读的兴趣与需求,而现代幼儿文学就建立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 中国现代幼儿文学的发生是一个过程,虽然可以有其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但绝不是在某一天突然诞生的,绝对的起点是不存在的。中国幼儿文学的真正独立与繁荣只有不长的历史,当然这是指印刷形式的幼儿文学,而在漫长的古老年代中,口耳相传的歌谣、神话、传说、民间童话、寓言等早已传入孩子的耳朵。不过,这些民间的歌谣和故事常常是面向所有人的,没有区分哪些是成人的哪些是孩子的。随着现代儿童观与儿童本位文学的确立,新式启蒙教育尤其幼稚教育的勃兴以及儿童期刊等出版市场的繁荣,幼儿文学不但从一般文学中独立出来,也逐渐从儿童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双重“异质性”的文学类型。其中的幼儿主要指学龄前的孩子,有时也延伸到七八岁的儿童,年龄只是一个大体的参照框架。 一 民间文学与蒙学教材探源 与世界儿童文学较为普遍的历史状况相似,幼儿文学的发展前史也大体分为两支:专门为幼童编写的书,多是蒙学教材而非文学故事,其中即使有文学的篇章,也往往意在教育;以及故事,但并非专为幼儿编写的。民间文学在被文字记载下来之前是口耳相传的,对于尚不识字没有独立阅读能力的幼童来说,对文学的接受主要便是通过“听赏”的方式,因此民间口头文学天然地与幼儿相亲近。 人类的幼年时代最先拥有了歌谣和神话,尔后神话逐渐演化出传说和童话。歌谣又称孺子歌、婴儿谣、小儿语、儿歌,是人之初最先接触到的文学样式。明代吕得胜《小儿语·序》()说:“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其流传特点在于“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被传唱了若干年代之后,有些歌谣才被慢慢记录下来,最早散见于《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等古代典籍中,明清开始出现专门的歌谣收集整理。吕坤编写的《演小儿语》()是我国第一部儿歌专集,内收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流传的儿歌46首,虽加以改作,但是每首儿歌的上半至少是原初的两句,保持了民间儿歌的原貌,下半改作意在“蒙以养正”,重视教训的同时能够兼顾趣味,在当时来说已属难得。 此外,明代文学家杨慎编纂的《古今风谣》两卷(),收录了上古至明代嘉靖年间歌谣余首,是中国较早的民间歌谣专集。此后常有采编的儿歌集问世,比如《天籁集》(,郑旭旦)、《广天籁集》(,悟痴生)、《北京儿歌》(,意大利人韦大利编选)等。年美国传教士泰勒·何德兰编的《孺子歌图》,内收首北京流传的童谣,中英文对照,在美国纽约出版。该书为每一首童谣配上了当时用“洋相机”拍摄的民俗照片,堪称中国最早采用摄影图片形式为书籍配图的出版物。从这些满蕴生活气息的歌谣里,编者读出了国人对于幼者的深情:“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喜欢儿童,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对中国的儿歌非常无知。我敢打赌,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能像中国的儿歌语言那样饱含着对儿童诚挚而温柔的情感。”这有助于改变现代人的一种偏狭观念,即认为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儿童在父为子纲的伦理框架下都是可怜的“受虐者”,而忽略了与此共存的“慈幼”事实。 《儒子歌图》ChineseMotherGooserhymes. ByIsaacTaylorHeadland.清光绪26年刊. 歌谣之外,老幼咸宜的听赏文学还有大量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山海经》和《淮南子》中记载了很多远古时代的神话故事,像“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与传说中的“牛郎织女”“大禹治水”等历代流传于大人与孩子之间。而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童话”,书中的《叶限》(又称《吴洞》)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灰姑娘型’经典童话,比法国贝洛于年所搜集发表的《鹅妈妈的故事》中的《灰姑娘》要早多年,比意大利巴西尔记载的灰姑娘故事也要早七八百年”。《搜神后记》中的《白衣素女》以及“狼外婆”等民间童话故事也多为幼童熟知。早在年,周作人的《古童话释义》一文中就已提出中国童话“古已有之”。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明)毛晋订 成人和儿童共赏的这些故事,后来很多被不断地改编,越来越成为儿童专享的故事,进而成为幼儿专享的故事,并以文字或图文并茂的印刷版形式被传播。而改编的标准就是“儿童化”/“幼儿化”和“文学化”,当然“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为时代的儿童观和文学观也在变。今天已步入读图时代,图画书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幼童阅读形式,但幼儿文学应保留“听赏”的观念与形式,不仅仅因为耳朵的倾听更能迫近语言的本质,从中获得愉悦的语言体验,而且纯文字的听赏是一种时间性的、线性连贯的阅读,与图画的空间性阅读不同,唤起想象的方式也不同。同时,它还能阻止一种不良的趋势,即在印刷文化成为主导之后,历史上有些曾被幼儿听赏的作品逐渐转让给了更年长的学龄儿童,阅读往往被窄化为“文字阅读”,误以为“看不懂的就听不懂”,这可能适用于成人或者能够独立阅读的年长儿童,但不适用于幼儿,因为幼儿看不懂的文字完全可能听懂。尊重幼儿文学的“听赏”特点,孩子们就会得到一份更为丰富、更有挑战性的书单,有助于避免孩子的阅读被进一步弱稚化和贫乏化。 此外,中国自古重视幼学,自汉朝一直延续到晚清的新式学校,专为教化孩童所编写的启蒙读物很多,而这些蒙学书中也隐含着幼儿文学最初的涓细源流。据考证,我国早在周代已有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史籀篇》,大约在13世纪南宋末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就是较早的一种,后经元、明、清的增删修改,又产生了一系列同类识字书。可见,古人很早就了解到图像对儿童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民国前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这种看图识字的卡片。很多蒙学读物虽不是以给儿童提供文学为目的,更不是为了孩子的娱乐而准备,但与世界上早期的儿童教育读物一样,它们大都是用韵语写成的,句式简短,朗朗上口,易于记诵,涉及天文、史地、人伦、博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广为流传。例如,从南北朝到清末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被誉为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千字文》这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做出的是“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这样美丽的文句,组成的是一篇文辞优雅、音节铿锵、条理分明、知识丰富、儿童读来琅琅上口的文章。蒙书这一特点影响深远,在年商务印书馆为初高等小学编国文教科书时,使用的仍是韵文,而出版后也获得一致好评。 《新编对相四言》祝氏藐园所藏.祝椿年跋.明刻本 蒙书中亦含有一些颇具文学色彩的故事,”为幼龄儿童而准备的故事书,在传统中国应从简化、改写的历史说起”。意即把历史简化成四字、五字韵语,以便于幼学者传诵。纯粹为儿童准备的故事书集在明代中叶以后出现,“更重要的,是至此以后‘故事’两字逐渐脱离历史掌故之说旧义,而衍为大家日后所熟知的撰说趣闻之意”。“故事”一词含义的变迁意义重大,摆脱此前作为“历史掌故”的观念束缚,具有了更广阔的驰骋天地,是在教化之外承担了“娱乐”的功能。明末至清代,各种教养并娱乐儿童的故事书渐增。以现存最早的版本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年)熊大木校注本《日记故事》为例,它有幅插图,每页上半截是图画,下半截是简要的文字说明,这不但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故事书。它记述了不少古代儿童的生活故事,多是可以启发儿童智慧的小故事,像“司马光砸缸救小儿”“灌水浮球”“曹冲称象”等,“大都是儿童自身的故事,所带的成人的成分并不浓厚,也不怎样趋重于教训。故相当的还近于儿童的兴趣”。这比西方第一本附有插图的儿童教科书——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年)早了多年。在漫长的幼学历史上,像《日记故事》这样上图下文、且富有童趣的启蒙童书,毕竟只是惊鸿一瞥。尽管从“图画”的地位来看,它与图文平等或图画占主导的现代儿童图画书还无法相提并论,但与《世界图解》一样,可以被视为儿童图画书的雏形。而从纯粹的教化转为教化与娱乐的并重,甚至扬娱乐而抑教化,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新锲重订补遗音释大字日记故事大成》 二 幼稚教育 为幼儿文学提供的契机 在清末民初的改良运动中,儿童从作为家庭中父之子、作为学塾中师长之弟子的偏私人化关系中走出来,成为民族国家的“小国民",其崭新的社会身份被建构起来,也因此被纳入“新民”的教育体系之中。其中,幼稚教育为幼儿文学的现代发端提供了新的契机。 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幼稚园、蒙养院的设立势必对幼儿教育内容、形式等提出新的要求,幼儿文学或者作为教育之辅助材料,或者直接充当一种教育力量,得以进入专业知识阶层这一现代“立法者”的视野。比如晚清大为流行的“学堂乐歌”,其歌词便是儿童诗歌。晚清诗界革命的中坚人物黄遵宪就曾以明白晓畅、活泼清新的笔调创作了数首学堂乐歌,其中《幼稚园上学歌》被周作人赞叹为“百年内难得见的佳作”,“不愧为儿童诗之一大名篇”。晚清的新学制导致了幼稚园、小学、中学等的分隔,这必然促发人们在提供给儿童教育内容时,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别。以曾志忞编辑出版的《教育唱歌集》为例,它包括了从幼稚园至中学所用歌曲26首,其中含幼稚园用8首,四个年龄段分别配以不同难度、不同主题侧重点、不同风格的诗歌,体现了随儿童年龄增长而循序渐进的特点。在此引录较具代表性的一首: 《老鸦》(幼稚园用) 老鸦老鸦对我叫,小鸦真正孝。 老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 小鸦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 自己不吃犹是可,母亲从前喂过我。 这首诗歌体现了曾志忞所倡儿童诗歌”浅而有味”的美学标准,即浅显而又有深意。《老鸦》的语言基本是口语的白话,借助幼童感兴趣而又容易理解的小鸦打食喂老鸦的形象比喻,进行了民族传统的美德教育,正是以“极浅”之文字,寄寓着“深意”。 民初周作人对童话与儿歌的研究,于现代儿童文学的确立功莫大焉,对当时新兴的幼稚教育亦有裨益。根据儿童学上幼儿的年龄特点,周作人指出:“幼稚园者,即据此性施以教育,玩具与童话实为其主要学科。故儿歌、童话玩具、游戏,在儿童研究中至为重要。”周作人主张幼稚教育应顺应自然,助长其发达,可是:“今人多言幼稚教育,但徒有空言,而无实际,幼稚教育之资料,亦尚缺然,坊间所为儿歌童话,又芜谬不可用。”所以他略论儿歌之性质,为研究幼稚教育者提供一点帮助。周作人对于童话与儿歌的研究,是采用民俗学与儿童学的方法,研究其文学属性与在教育上的应用,可谓空谷足音,但也因为太超前而未引起广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anxizx.com/xxzx/13320.html
- 上一篇文章: 陕西地方端午节习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