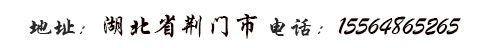陕西历史文化研究刍议
|
大家都讲陕西的文化建设,陕西的社科界义不容辞。陕西文化不单是陕西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陕西一般来说有三个圣地,人文圣地黄陵、革命圣地延安、农业圣地杨凌。实际上这三个圣地将产业、时代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红色文化都有兼顾。当时我提出杨凌是农业圣地之后,好多媒体人想把这三个圣地串起来讲,用一个比较大的、占有一定分量的媒介形式将它推出来,但是这些年看起来好像没有把这事做成。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曾讲过,陕西是天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有了这两个,实际上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已经大致可以确定下来了。 关于这些表述,陕西学界已经有过一些总结与归纳,但是我们陕西的宣传在这一方面没有把这些学术研究变为文化表达。比如杨凌农业圣地提出来以后,杨凌至现在还习惯叫作农科城、后稷故里、绿色硅谷,农业圣地的说法还是局限在学术圈子之内。不过我始终认为最能提神的恐怕还是杨凌是中国农业圣地,它是中国农神出生的地方,并且四次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肖云儒作为陕西有名的文化人,他讲到陕西文化时用了八个字,他说陕西这个地方是萌易、生道、立儒、融佛之地。中国传统的哲学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道家学说在这里生成。儒家学说源头在这里,立学派确实是在山东,但是成为国家学说是汉武帝把它立起来。我们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学说,实际上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融佛之地,佛是西天的,但是佛教除了南亚的原始佛教外,现在流行于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的都是中国佛教。早期可能有矛盾冲突,但是后来变成宋明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讲中国化,如果有一个参照,那就是佛教是怎么样完成它的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是翻译与介绍,到后来是义理阐释,由高层人士的接受再到普通老百姓的信奉,这是外来学说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路径轨迹。 我们过去文献上讲中华五千年文明,现在榆林的石峁和延安的芦山这两个遗址被发掘以后,甚至按照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无法予以解释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可能还要往前推。石峁那么大的一个工程,是天文数字的土方量。有一次在东北师范大学开会的时候我讲到,文明很可能是在不同产业类型交接地带出现的。在同一产业内部突破不了血缘的关系,只有在边缘或交接地带受到挤压、矛盾与冲突的时候才会促使某一种权威的形成,这样一种推断现在看来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陕西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做些什么事,我想有这么几个领域可以研究: 第一个是周秦汉唐研究,肯定是我们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陕西搞历史的人可以研究宋元,也可以研究明清,但是占主导的一定是周秦汉唐。西北大学、陕西师大不能跑这个题,如果跑题相当于把我们的长处放弃了。这里面可以研究什么内容呢?可以研究盛世规律,周秦汉唐建立时是哪一些要素,使得当时社会能达到极盛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个是大国治理模式,我们可以讲中央集权的不好,但是在当时实际上它是有效的。汉初也曾试行过郡国并行制,但在文景时期就出现了问题。谭嗣同、毛泽东讲“百代皆行秦政事”,我们应该在大一统的大前提下考虑其中有效的方面。我们陕西人在言及陕西历史文化时,都会讲到长安乃十三(四)朝古都。我在《秦岭历史文化解密》中讲到,光是择都关中这个地方,即可见先民的远见卓识。一个地方一次两次作为首都具有偶然性,若十三次为都绝对有其必然性。它的必然性就在于张良提出的八个字:形胜之地,天府之国。我们的选择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就绝对有问题。我们把京畿放到开封以后,平原城市无险可守,禁军数目增多殿前都点检权力太大,导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守军少一些,少数民族进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抓走了,“靖康之耻”。“形胜之地,天府之国”,我们的老祖宗用八个字把一个国家、民族选择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最基本问题解决了。所以周秦汉唐不是说我们研究多了,而是现在看来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够,这是我们陕西人文社科界应搞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研究我们陕西人应该有所担当。丝绸之路的研究很多,但是许多人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还是立足于能争取一些项目、一些经费而已。所以我一直讲,陕西社科界应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上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尤其出一些思想,出一些观点。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乌鲁木齐、兰州是过路城市,不是起点。我们西农的几代人,从石声汉先生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研究丝绸之路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几代人几十年把引进来的东西输出去的东西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如果对这一问题有所推进话,那就是除了起点以外,明确了落脚点的说法。出去的时候是起点,回来的时候是落脚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讲到,许多引进来的东西“植土秦中,渐及东土”,在这里种一段时间再推广到全国。看起来我们提到一个落脚点,形成一个闭回系统,陕西的地位更加突出。另外我们还提出一个问题、发现一个规律,即丝绸之路的盛通衰闭。这条路凡是到了盛世就通了,凡是到了衰世就不提了,我们在坐的都是搞历史的,一想确实如此。 第三个西向发展的问题。一讲到周秦汉唐以后,陕西人的底气就不足了,实际上最近弘扬交大西迁精神的活动很有深意,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还不到位。提到宋以后,我们陕西人一点也不要自卑。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放到东部是宋代以后东向发展格局确定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只能是效益优先,在上海的投资肯定比在西安的投资效益要高。我最近给兰大写的“独树一帜”的坚守,在胡焕庸线的西边,“双一流”只有一所兰州大学,以此凸显这所大学的担当与坚守。不可想象,如果这些年没有兰州大学及兰大人在西部的坚守人,我们的西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兰大人是应该能感受到这一提法的分量。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东移以后遇到的很大问题是西边、北边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所以始终关照西部。历史地理学的西北舆地学的兴起,反映了对西部边疆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anxizx.com/xxzx/10513.html
- 上一篇文章: 陕西光大药业集团下半年最新上市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