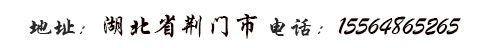那一年,陕西的饥荒几乎无人看得懂的
|
席有生的母亲席王氏只有像所有移民一样变卖家中包括被盖、衣服和桌椅板凳在内的所有财产,到占有好土地和浇灌条件好的当地人那里去换粮换瓜菜——一件衣服换一斤箩卜白菜,一张桌子只能换两三斤面粉。到了基本上是倾家荡产时,席王氏便把当地人抛弃的糠壳和空玉米棒拾来磨细做成馍吃,或者到荒滩上挖来一种叫黄角粮的药材,剥皮泡三五天去掉麻性再吃。但这些都是具有危险的食品,吃后拉不出屎,得用棍子掏。 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糠壳……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席王氏常到黄河边去寻些枯野菜,或者去拣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干莲花白叶子,用水泡泡,然后和着带壳的糜子面煮成一锅能照起人影的糊给一家人充饥。即使这样的食品,也不能保证一家人吃饱。席王氏为了让丈夫、儿孙们多吃一点,她常常把“糊”煮好后就借故去做这做那地忙着,或者舀上一小碗躲到一边吃。实在饿得慌了,她便按照乡亲们介绍的方法,把辣椒磨细,冲一碗开水喝下,让辣的感觉麻醉空空的胃囊,暂时忘饥饿的折磨。不到两个月,席王氏骨瘦如柴。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席王氏去挖老鼠洞,抓老鼠给家里人加强营养。去世的前几天,把手伸进洞里抓老鼠时被老鼠咬了一口,没有钱看伤,伤口感染了肿得老高。这样一来,她更加虚弱了,在家走路要扶着墙,在外找野菜拄着木棍还常常被大风刮倒。年阴历2月初7,阳光明媚,无风。但在寻找野菜的路上,席王氏仍然倒下了——她不是被风吹倒的,而是饿得发晕,一头栽倒的。若像平时那样倒在沙地上,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每次被风吹倒,稍过片刻,她就能依靠手中的棍子慢慢站起来。但这天,席王氏却倒在了水渠里。水渠里没有水,但淤泥死死陷住了她的双脚,她用带伤的手挖开淤泥才好不容易取出了一只脚,另一只脚挣扎了很久都拔不出来。她曾经呼救,但虚弱的她喊出的声音那么微弱,根本传不远,更何况,荒原上当时根本就没人。当天中午,临村的人发现时,时年51岁的席王氏仰卧在渠中的淤泥里,她的生命已一点点远去——一滩淤泥,成了压垮她生命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一只脚仍陷在淤泥里,那只被老鼠咬伤后肿得老高的右手沾满稀泥,左手紧紧攥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点不多的野菜。她脸上充满忧郁,两眼圆睁。”49年后,席王氏这个被历史雕塑得最完美无缺的悲剧形象依旧清晰地保留在儿子的心目中——已74岁的席有生提到母亲死亡的姿态和表情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我去收尸,怎么也取不下她手上的篮子,也无法使她闭上眼。我知道,妈是放不下我爸我妹和我这一家人。她想用那点少得可怜的野菜解除饥饿对一家人的威胁,死亡之神却以这种方式宣布她从生命的舞台上出局……”如今已年近六旬当时还不满八岁的席宣花对母亲的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但她却牢牢记住了母亲死后的情景。按家乡的习俗,在外死去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席家只好在村外搭个棚将席王氏的尸体停在那里。席宣花不知道妈妈已离开了他们,还天天去摸妈妈的脸,去拉妈妈起来煮饭,说自己饿了。直到母亲入葬那天,席宣花才突然明白了死的含义,她扑在妈妈的棺材上撕心裂肺地哭喊:“妈妈,别走呀!我饿,你走了谁给我们做饭啊……” 母亲去世后,席有生的婆姨谢翠花被推到了家庭主妇的位置。当时,刚满20岁的谢翠花是一个漂亮、矜持、柔弱且极爱面子的少妇。不久,无米之炊的苦恼使她意识到,当贫穷、饥饿时时相逼之时,人的尊严、人格和面子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她不仅继承了婆婆饿自己,顾家人的品质,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拿起讨口的篮子和打狗棍,走家串户地去乞讨食物,用自己那瘦削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家里人挨饿,更不能让家里人饿死。每天天不亮,谢翠花就用小车推着一岁多的女儿英子去挖野菜,然后推着小车从冰上过黄河,到黄河西边的贺兰县去讨饭,中午前后,她准会回到家中用挖来的野菜和讨来的食品给一家人煮一锅饭充饥。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她便出门。并走到贺兰很远的地方去讨到了较多的食物。这样的幸运并不长久。年农历11月下旬,工作组对谢翠花经常过河的那个地段实行了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设卡,谢翠花的乞讨之路再次被阻断。谢翠花要去贺兰乞讨食物救活家人的决心并没能被阻断。她决定另劈过河的途径。席有生听了婆姨的决定坚决反对,“千万不能冒险去另外找路!去年以来,好多先遣队的人走白冰掉进黄河,至今仍尸骨难收!”席有生的话并非吓唬妻子的无稽之谈。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趁着夜色偷渡冰封的黄河,浮冰断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华阴县百洛村一个叫王新年的年轻人刚从部队复员就带着妻子、儿子到了陶乐。因不愿饿死异乡,年隆冬的一天晚上,他带着妻子和三岁的儿子,准备过黄河逃回陕西。行至河心,突听脚下的冰层发出了可怕的“咔嚓”声。王新年知道不好,惊叫一声,抓住老婆的手想跑,但已来不及了,不堪重负的冰层瞬间塌陷,一家三口被黄河吞没。次年春暖冰融,人们在黄河里发现了这不幸的一家:王新年挑着担子,手牵妻子,妻子拽着儿子,三口人以奔跑的姿势,在水下保持着令人心酸心碎的造型…… 某村那13个冤魂及王新年一家悲惨的故事并未吓退谢翠花。她安慰丈夫说:“放心吧,目前已是隆冬季节,河里的冰越来越厚。更重要的是,最近多次过黄河,从当地人那里学了不少过河的知识。比如,分开行走,莫挤一堆。比如,走青不走白……”她问丈夫:“知道为什么要走青不走白吗?”席有生茫然地摇摇头。谢翠花得意地告诉丈夫:因为冰层颜色发青的地方就表明冰已结得很厚了,行走在上面就不会有危险。而发白的地方,就表明那里的冰层还不厚,朝这种地方走准会掉下去……有丰富冰上知识的谢翠花还是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她和女儿走了“白冰”。几十年过去了,席有生仍然准确地记得黄河吞噬他婆姨和女儿英子生命的时间,“那天是年农历11月26日。”与谢翠花一起的乞讨者告诉席有生:那天,谢翠花的运气不错,讨到了好几斤黄豆。她兴冲冲地用小车推着英子往回走,说要给家里人做顿豆花饭吃。结果,她慌不择路,忘记了走青不走白的过河秘诀。小车压裂了冰层,车上惊愕的女儿还没来得及哭出声来就“嚓”地掉进了黄河,谢翠花“啊”地尖叫一声扑上前去营救女儿,但她没能抓住女儿反倒压裂了身下的冰块。同行的人说:“掉下河后,她只冒了一下就不见踪影……”年4月,打鱼的人从河里捞起了谢翠花的尸体,女儿的尸首则不知去向。已家徒四壁的的席有生用一床破棉被掩埋了自己的婆姨。没有家庭主妇的日子使席家从此失去了重心,倍感迷茫。席兵的身体原本非常健壮,在老家时,他能挑着多斤的竹货在一天之内从朝邑赶到60多里外的华阴去卖掉,然后再赶回家里。一年四季,天天如此。重体力劳动也使他非常能吃,一天能吃十斤膜,晚上从朝邑回家,还能吃一小盆面条。到陶乐后,粮食的奇缺使他不得不以紧勒库带的方式节食,即使这样,他的饭量仍大得惊人,有一次,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折磨时,他问妻子:过来几个月了,一直都饿着,能不能让我吃一顿饱饭?席王氏默默地流着眼泪把一家六口的饭舀给了丈夫。席兵吃完一家人的那顿饭后流泪了。那之后,一种罪过感老堵在他的胸口,使他心神不宁,不管家里人以什么方式让他多吃一点饭菜他都会拒绝。长时间的饥饿使席兵的身体很快虚弱起来,特别是妻子、儿媳相继去世后,家里连野菜糊都没有保证了,他周身的浮肿开始加剧,手、脚“胖”得吓人,长期卧床难起。最让席兵揪心的是,家中无隔夜之粮,九岁的女儿席宣花外出乞讨挖野菜不是被狗咬便是跌得伤痕累累。又过了不久,连席宣花挖回的野菜也没地方煮了——当时,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墙壁上、山石上到处都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我家!”“人民公社万岁!”的口号。迁往宁夏的关中移民也按照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公社之内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的要求效仿起了“大而公”的公社化生活。吃大食堂,统一劳作,统一分配成了那个时代农村最时尚的生产生活模式。家家户户的锅都被收去炼了钢铁,社员们集中在公社的食堂里,每天都凭借三碗稀粥两个馍维系着生命,也维系着人民公社艰难时期的“大好形势”。一天,饿得头昏眼花的席宣花说了一句让父亲心惊胆颤的话:爸爸,让我死吧,我死了你就可以一个人吃四个膜了。席兵不安起来。他已听到了太多为了一顿饭、一个膜而亲情冷酷无情,骨肉亲人自相残杀的事情:一个叫薛辛友的汉子,在饿得发昏时,只因六岁的儿子老啼哭着问他要饭吃,他发怒了,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随即自己也成疯癫。几天后,这个“杀人凶手”饿死于拘留所,紧随着无辜的儿子相会在另一个世界……在离席兵所在移民村不远的何家庄村,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哭着问他妈要饭吃,已饿得奄奄一息的妈妈已拿不出任何东西给儿子吃。情急之下,妈妈打儿子一巴掌并骂道:催命鬼,早晚都要饿死,自己去死吧,还要吃什么饭……“死就死!”倔强的小男孩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了村口的大树上。他母亲知道后也当场气绝身亡,于是,吊在树上的小男孩连个收尸的亲人也没有,在树上整整吊了一天……为了不让女儿重蹈那两个小男孩的旧辙,席兵做出了一个他十分不情愿的决定:卖掉女儿,给她一条生路,也给自己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一个姓蒋的人同意用斤面粉“换”席宣花——席兵还想再多要点粮,可那姓蒋的说,斤面粉换你一个女娃已很亏了,华阴土洛坊村的朝老头把他儿子朝耕喜30元就卖给了朝新朝。一个当地人用70斤豆腐渣就换了一个小女儿,你要价这么高,我得考虑要不要你这个女儿了……怕蒋家反悔,席兵赶紧同意。年3月的一天,席兵把从人民公社食堂领来的那个窝窝头塞给女儿说:妞儿,去给蒋叔当女儿吧,今后你就有饭吃了!有了面粉,席兵的生命历程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回光返照”。他可以下床拄根棍子行走了。无风的日子,他还能步履蹒跚地挪到移民村落的那道土墙根下蜷缩着身子同那些与他命运相似的老婆老汉们一起晒太阳。在那道土墙下,席兵不断从那些说话已口齿含混不清的老头老太婆们那里听到不少与粮食相关的悲剧故事:什么百洛乡的安东来、李新力为了不让一家人饿死,在生产队偷粮斤被判3年呀,什么某村一老汉,吃了糠皮馍肚胀拉不出屎还嚷着问儿子要了碗面条吃,结果被撑死了呀……但最令席兵惺惺惜惺惺的还数华阴南洛乡义和村那个叫石光兆的孤寡老汉。石老汉已70岁却饭量大得惊人,他把一个月的5斤面粉从村里的食堂领去两顿就吃完。接着,他又寅吃卯粮,把下一个月的5斤面粉也领去两顿吃完。食堂再也不给他发粮了——石老汉四顿吃掉了两个月的定量,也吃断了自己的命脉——一星期后,他饿死在床。令席兵伤感的还不只是这些——前不久,由于到墙根下来晒太阳的老哥们儿老姐妹们多,位置还有些挤。可两个月不到,蹲在墙根底下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他们都已到村外沙丘下的新坟堆下永远“晒太阳”了。剩下的这些老哥们儿老姐妹们也都同自己一样周身发肿,四肢无力。他在心里估摸:大家到村外沙丘旁那新坟堆里“晒太阳”的时间也都不会太久了……果然,斤面粉吃完不久,席兵不能到墙根下晒太阳了。极度的虚弱和日渐沉重的病体使他预感自己已来日不多。他想女儿了。但无力抚养女儿的无奈和将其当作廉价商品出卖的疚愧使席兵不敢提出让女儿前来相见的要求,他担心女儿不会认自己这个无能无情的父亲,更不会来给自己送终。不过,将死之人最终还是没能遏制住自己越来越强烈的舔犊之情——他不想把对女儿的牵挂肚和担心、思念、忏悔之情带进坟墓。席兵托人把女儿从蒋家叫了回去。席宣花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自己那天回家时的情景:哥哥到青风峡抬石头去了,躺在床上已动弹不得的父亲想喝水,可家里没有,席宣花到村头的井里用破盆端了点。她本想给父亲烧成开水,可人民公社的食堂已把所有锅、壶收走。她刚要把破盆架到灶上烧,父亲忙阻止,“别点火,房上冒烟,那些……干部又要来……找麻烦!”家里已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不知怎么办的席宣花呆呆地坐在床前,天黑后,就靠在父亲身边睡下。半夜,席兵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问饿醒的女儿,“妞儿,什么时候了?”席宣花告诉父亲,自己也不知道。“妞儿,把你卖给蒋家,怨爸吗?”“不。”“不就好。只有你……这么个妞,爸也……舍不得。但爸这里……没活路呀!”席兵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停了停,情绪稍稳定些,知道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席兵开始交代后事,“妞儿,告诉哥……今后一定……要把我和你妈、你嫂子……迁回陕西!不要让我们……在他乡……当野鬼……”席宣花不明白父亲的话,“爸爸,你怎么会当野鬼呀?”席兵喘着粗气对女儿说:“你不懂……给哥哥说……他……他明白”。说完,席兵拼尽全力慢慢地一点点地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女儿,然后问:“妞儿,我的脸……是不是背着你的?” 从席宣花的回答中得到证实后,席兵安静地“睡着”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席兵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完成了一个转身动作,把脸背朝着墙壁,避免死后吓着女儿,以此表达出他最后的舔犊之情,把生前的情感和死后灵魂永远地留在了女儿的心中…… 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anxizx.com/xxzw/6864.html
- 上一篇文章: quot我的驻村扶贫日记quot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